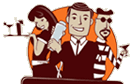 爱尔兰各地有数不清的酒馆,从旅游者必到的都柏林酒吧,到乡野小镇上的本地人酒吧,以及音乐家们自己经营的充满音乐气息的酒吧。形形色色,这都是凯尔特后裔的心头好。
爱尔兰各地有数不清的酒馆,从旅游者必到的都柏林酒吧,到乡野小镇上的本地人酒吧,以及音乐家们自己经营的充满音乐气息的酒吧。形形色色,这都是凯尔特后裔的心头好。
爱尔兰的酒馆大多光线黝黯,但气氛温暖。人们拐进门来,乒地一声关上门,就好像一种感情在合适的时机潜入心灵一样,他们嵌入带靠背的木椅或者椅面凹陷的高脚凳,不偏不倚地将自己的臀部嵌入椅面的凹陷中,落座在那里。
爱尔兰各地的酒馆里大多挤满了人,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,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,只要走进酒馆,你就是个酒客。有种奇异的知己的气氛,随第一杯黑啤酒在纸杯垫上推到你面前而油然升起,它轻易将一切陌生感消除。因此,人们总是评价说,爱尔兰的酒馆的气氛是友好的,人们在此敞开心扉。这种敞开,并不是要痛说个人历史,而是一种微妙的、感情上的开放,你可以一言不发,但你仍感到自己已渐渐融入四周,你看着别人呼朋唤友,并不会觉得有压力,因为你也不是个陌生人,你只是有点沉默而已。
那里总是烟雾腾腾的,众生喧哗。够历史的酒吧,靠窗的一溜,通常有密室。那些用深褐色的橡木板与店堂隔离开来,并在橡木板上方装饰着彩色玻璃窗的小隔间,是爱尔兰传统酒吧里的特色,人们称它为snug。它们又小,又温暖,天光透过那些彩色玻璃,令那些古老的私室里斑斓而脆弱,好像内心在感到舒适时漂浮而过的情感。那里好像专门就是为沉湎于内心建造的私室,让人想到,流连在此的人们都有敏感的内心,那个隐藏在胸腔里面的世界时常需要安抚。
snug里有人吸烟,有人打嗝,有人突然高声笑了,是个女人响亮的声音,好像小石头从山崖上清脆地滚下来,从花窗玻璃后传来。
在一家大西洋边的小酒馆里,傍晚时,天光仍旧清亮。店堂里渐渐坐满了人,各处散发出了黑啤酒的生面团气味。我前面挤着十几个穿着一模一样黑色T恤衫的美国人,他们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旅行团,在我前面欢声笑语。店堂中央,有另外一支旅行团,是从英国来的,它的特色是团员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,寻常打扮,领头的却是一位又瘦又高的男人,好像童子军里的老师。她们热烈地互相交谈着,大多数人都很乏味地喝着一杯白葡萄酒。
……
也许爱尔兰的古老曲调,真的可以追溯到莱茵河中部那些叫塞壬的水妖,那时那些迷人的曲调能使过路的水手丧命,现在,即使是在酒馆里,还是能迷惑住萍水相逢的人们。我突然想起我从前的一个老朋友,他有许多年患广场恐惧症,一个大男人,却不敢离开家一步。即使是他,也被爱尔兰乐曲迷住了,像一只被蜘蛛紧紧织进网内的蚊子。
某个下午,多雨潮湿的西港正阳光灿烂,这里的旧港口处立着纪念碑,纪念土豆饥荒年代从这里出海逃生的爱尔兰人。纪念碑是一艘青铜制成的鬼魂船,当年人们仓促入海,其实许多简单的木船根本经不起大西洋的风浪,那些船从未到达彼岸,人们随之葬身海底。人们称这样的船为鬼魂船。
城中的麦特·马龙酒吧里间,如酒吧的私室那样温暖黝黯,人们知道麦特今天下午会来演奏笛子,就聚集在那里等着。其中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笛子手,还有个十个月的小女孩。老笛子手还在找合适的古老曲调填词,创作新的民谣。小女孩柔软的亚麻色胎发上结着一只沉甸甸的粉红色绒布蝴蝶结,好奇地等待着。她年轻的父母看上去像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,带着尊敬和喜爱,微笑地望着和乐队坐在一起的麦特·马龙。
桌上,黑啤酒表面上那一层白色泡沫经久不散,好像新鲜面包瓤子一样。这时,也像有只白色的鸟一头冲进阴沉的天空深处那样,一个高亢而柔和的声音冲破酒馆里弥漫的嗡嗡声,它的清亮里,有单纯,婉转,欢欣,顺从,和怀旧的感伤,这是麦特·马龙的笛声。
他偏着头,像一只大鸟偏着头,聚精会神倾听遥远的声音。笛声渐渐悠长,仿佛遥远地方的呼唤,他扬起脸来,打开双肩,好像承接住那些从空中落下的音符。他的胡子白了,他的眼睛里有显而易见的失落与感伤,这天是他妻子去世的周年纪念日,追思会刚结束。
从波莱夫尼十岁时在自己班上见到他,听到他为小孩子们演奏笛子,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。
麦特·马龙转眼已吹奏了大半生爱尔兰笛子。
他家的男人,从他爷爷开始,就喜欢吹笛子。接着是他爸爸,爸爸已在家乡的酒馆里演奏。家里常常充满了笛声。他还从未想到过此生要做其他事的时候,笛声就已顺理成章遍布他的整个生活。他也从小就吹笛子了。一代又一代,马龙家最容易找到的,就是笛子。马龙家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并无太大变化,所以,麦特的儿子,如今也是笛子手。
麦特因此学到了许多爱尔兰传统的曲调。他从未想到过会钟爱其他曲调,爱尔兰的古民谣就像海洋包围小岛一样,将他包围在这一次生命中。
一个简单的机会,他去了都柏林,他在那里参加创办酋长乐队。这支乐队是六十年代改编爱尔兰传统乐曲、推动爱尔兰民谣走向世界的重要乐队。他们使古老的爱尔兰民谣,从世界尽头遗世独立者的清澈吟唱,变成能俘获世界各地无数心灵的仙乐。

这种对爱尔兰民谣的钟爱从贝多芬时代就已经开始,当《玛尔塔》里的玛尔塔唱起由古老民谣改变的《夏日里最后的玫瑰》,全世界都响彻了爱尔兰忧伤而又甜蜜的声音。麦特说,他们的乐队只是那旷日长久的钟情中的一步台阶。
在爱尔兰,人们总是改编那些古老的曲调。那些悠扬的曲调中,人类的感情和心灵似乎一次次超越时间,像穿过珍珠的那根细线那样。这是我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、对时间和传统的理解。时代的更迭并不能使人的感情过时,只能使它日益显现出相对流逝的永恒。
在爱尔兰,似乎人们理所当然地珍爱自己的传统,他们与古老而迷人的一切息息相通,从未感觉到传统的压迫,制约和禁锢,他们在那里看到的是,就是永恒。这是令我羡慕的与传统的感情。
麦特这一生吹的笛子,是他爷爷的笛子,也是他爸爸的笛子。他手里握着笛子时,好像那笛子是他肉体的一部分,那样的熟悉。他一生吹过的笛子曲,是爱尔兰人世世代代吹奏的曲子。
“从未觉得过自己的生活太简单了?这一生里,似乎没尝试过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”我问麦特。
“不。”他晃动了一下肩膀,似乎要确定是否自己坐得舒适。然后他说,“我很安适。”
麦特想了想,又说,自己这一生一切都好,只是旅行太多。在世界各地演出,他老是在旅行中。有时他想静下来,只在家里静静住上一阵。或者驾船出海,除了笛子外,他最大的爱好是航行。这也是一个地道爱尔兰人的爱好。
比起中国人,麦特是一个非常、非常幸运的人。在爱尔兰,连圣人帕特里特传教,都将天主教的十字架上加上一个凯尔特圆环。虽然世事巨变,但爱尔兰人始终生活在迷人的老女士身边,吹着祖传的笛子,安顿在爱尔兰男人的角色中,并接受自己的命运,而我们,却只有七零八落的遗迹,与躁动犹疑的抗争。
麦特和三个年轻人一起演奏一支古老的爱尔兰民谣。在竖琴和提琴声中,笛声清亮地浮动,像黛绿色的森林中央围绕着棕色的湖泊,白色的天鹅在如镜的渊面上滑动。麦特偏着头,这次,他好像一个热恋中的男人正俯身去倾听他情人的心跳。
那个十个月大的小女婴,被她父亲双手抱扶,站在麦特对面的地板上。她随着节奏舞动双脚,她无声地欢笑着,大张着粉红色的小嘴,流了一下巴亮晶晶的口水。她毫无保留的欢笑,让我想到十岁时的波莱夫尼。当他在依尼斯的小学教室里看到麦特时,大概也是这样惊喜地欢笑着的吧。
幸运的爱尔兰音乐,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我是在麦特在西港的那家有爱尔兰传统音乐表演的酒馆里,学到“传承”这个词,其实含有真挚的感情,而不是冷静的利用。爱尔兰有个昵称,叫做迷人的老女士。我在麦特的笛声中突然明白过来,人们如此称呼这个国家。大概不光是指它古老优美,历尽沧桑,还指它仍旧受到宠爱与怜惜,仍令人为之着迷。如果有人宠爱一个老女士,她也许能比其他女人更迷人,因为她醇厚。
清澈与醇厚在一起,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美德。
鲜花速递网www.maihua.me版权所有,转载敬请注明。
(本文节选自陈丹燕新书《我要游过大海》,2010年5月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
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